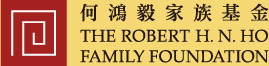一連數篇文章對禪僧的象徵授禪方法作了引例探討,本文主要簡單分享另一些零碎卻又常見的禪意象元素,以及對此作簡單小結。
1. 其他意象
禪宗教學所運用的意象,當然不止於筆者所舉引的種種例子,禪錄中還有很多。一些幻物意象群,如夢、泡、影、鏡等,用以形容心因緣境而呈現不實事相,深含萬法虛妄不實、生滅無常之義涵。禪師對之繼承並加以創新,後來出現溈山與香嚴之占夢公案、啞子禪林得夢等故事,強調悟法不假外求和自悟成佛之重要;而泡、影等幻物意象則更多地作為自身虛幻常變的象喻。《大乘起信論》之「四鏡」概念,以鏡喻心,認為眾生心如明鏡,本來空寂而能映照萬象,無有差別。他們亦根據鏡玲瓏明晰之特點,象徵人本具之清淨佛性,能自然存在而照萬象;然若執於打磨或刻意修飾,反使明鏡無光,借之以顯示道不用修之禪理。
此外,禪宗塑人意象群亦為其特色教學工具之一。所謂「塑人意象」,指禪僧說法時為了把抽象禪理具體化,而塑造出一些具體人像作為傳禪工具,這種塑人意象獨於禪宗語錄中常見,具有生動的藝術形象。例如臨濟宗的「無位真人」,往往象徵已超越凡聖、迷悟等分別而無所滯礙之人,是用以借喻徹見本來面目、已達解脫者之典型意象。又如「無依道人」,表示無被任何外在條件束縛之人,揭示在塵出塵、處萬境而無所依之修禪法門,並借以象徵遠離煩惱繫縛之清淨境界。此外,「屋裏人」、「主人公」等都是禪人常用之塑人意象。禪僧以「屋」喻軀體、「人」和「主人公」象徵人人本具之佛性,透過「屋裏人」這種意象語言突出眾生是佛、即心即佛之禪意。
禪宗是生活化、現實化的佛教宗派,在叢林修持的過程中,所觸之物皆是教材,於是便有不少生活意象群的出現。如「橋水流」、「饑餐困眠」、「屙屎送尿」、「吃茶」、「洗缽」、「麻三斤」、「庭前柏樹」、「乾屎橛」、「下藥」和「治病」等,都成為禪僧的教化取材(可參《祖堂集》和《景德傳燈錄》)。
除形象化、具體化的意象外,聲音的虛妄不實,存而虛有,能聞而不能觸,無形可見,成為禪師以之作為真如法相的載體而點撥學人的對象,這亦是值得探討的。如鐘鼓聲為禪院報時或通告之訊號,禪僧以聞鼓歸家、饑來吃飯象徵平常心之道;雨滴聲以鏡清道怤一段公案成為禪僧說法的流行題材,突出撇除內外二見、使心中無物之禪義;香嚴智閑因以瓦礫擊竹作聲而得悟,表達「不見非不在」、「禪悟無形而在機」的禪意義,成為了「竹聲」意象形成之因緣。
2. 小結
一般認為,禪悟是一種中國佛教獨有的非理性神秘主義,也是一種具有強烈主體意識的宗教體驗,其以典型直覺思維方式呈現出超邏輯知性的嶄新語言面貌,為我國美學、教育法方面提供了重要養份。意象作為傳意的工具,具有非功利性的特質,正如柏巖明哲云:
「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定州柏巖明哲禪師〉,道原編,《景德傳燈錄》,收《大藏經》,第51冊,卷7頁253a)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在《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以月亮為例道:
「月亮是一個觀照的對象,卻從來不是欲求的對象。」(叔本華著,劉大悲譯,《意志與表象的世界》(臺北:志文出版社,1974),頁136)
師生教學活動間以意象作為象徵,在對答中加以援引以啟發學生,教學對話中所運用到的這種意象,同樣是非功利性的。
對此,周裕楷先生《中國禪宗與詩歌》一書有很獨到的敘述。其大作的第九章清晰地指出,禪與詩具有:(一)「價值取向的非功利性」。禪宗反對學人從語句上拘囿探求,黃檗希運云:
「我此禪宗,從上相承已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筠州黃檗斷際禪師〉,賾藏主集,《古尊宿語錄》,《續藏經》,第118冊,卷2頁182a)
說明悟道方法與內容無法通過分析可得。我國詩歌則重於「韻味」、「神韻」,所謂「詩無達詁」,對待詩歌,讀者往往只能體驗冥契,無法透過分析得到詩髓,周先生指出:
「正是由於詩禪本體的這種特性,所以禪僧的參禪悟道以及詩人的審美活動,都是借助於形象,而不是概念。……禪和詩都以形象為中介,都以非概念的直觀體驗為手段。」(《中國禪宗與詩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304)
因而禪與詩具有(二)「思維方式的非分析性」。此外,周氏認為,禪的目的在於追尋本體論水平上的「悟」,而不是知識層面上的「知」;有如詩的目的是追求現實世界藝術意義上的「美」,而不是科學意義上的「真」,因而兩者具有(三)「語言表達的非邏輯性」。最後,他指出禪與詩都具有很強的主觀精神因素,因而兩者都具有(四)「肯定和表現主觀心性」的特點。(《中國禪宗與詩歌》,頁297-319)
這四種特點恰到好處地概括了禪與詩的關係。在此之外,詩禪相通還有一項特徵,就是「意象運用的象徵作用」,這在我一連幾篇文章中,已有所展示和論述。
討論禪僧以象徵方法授禪的特色到了結尾部分,有一點不得不釐清的是,縱然禪宗強調親證實踐,以直了心性,見性成佛,但是他們這些提議的前提,並非旨於摒棄一切非實踐性的學習認知行為。我想說的是,禪宗絕不是「極端行為主義」的提倡者,其教學的立場也不純粹單靠直接經驗去釐定。觀察學習(Learning by indirectly experience)自然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只是,對於禪悟情志,缺乏親歷學習(Learning by directly experience) 的經驗,是無法達到最深切和最完備的禪悟體會。例如有人吃雪糕吃得津津有味,我們尚且能憑經驗或對雪糕本有的認知去估計吃者的感覺。然而,禪門所謂「畫餅不充飢」,假如該雪糕已嚴重變質,只是吃者給我們一種假象,我們壓根兒無法得到吃該雪糕感覺的真實。
不過,禪宗強調的親證實踐,並不是要我們每個人都走去拿這個雪糕吃一口,這種推論是一種盲目的迷思(俱胝之所以斷指,就是他無法意識到自己苦陷這種迷思之中),有違原意,也不切實際。反而,禪宗的智慧在於,她強調我們不是要直接模仿,反而是要在替代學習(vicarious learning)的原則下實現有限度的抽象模仿(abstract modeling),也就是從對吃變質雪糕的事實中,學習到「要感受吃的感覺必須親自去吃」的抽象原則一樣。這其實好比加拿大教育心理學家愛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強調的一種高層次模仿的社會學習論。Bandura(1941)曾指出,人類在社會中受到個人、行為與環境因素相互影響,產生模仿的行為。模仿行為包括直接模仿(direct modeling)、綜合模仿(synthesized modeling)、象徵模仿(symbolic modeling)和抽象模仿(abstract modeling),四種模仿有認知上的不同層次的劃分。就此而言,學人盲目跟隨禪師坐禪修行,或盲目豎指大喝,顯然只停留在第一種直接模仿的層次。綜合模仿是禪僧在認知行為上的經過若干篩選,綜合成為個人的模仿學習方法而形成,層次自然較高。象徵模仿和抽象模仿則可以說是禪宗象徵教學法主要說明的內容,學人所學習的,已非具體行為,而是行為背後所代表的義涵和抽象符號,過去一連幾篇所描述的象徵意象,實際上屬一種高層次的觀察學習,其討論核心也就在此。
那麼,有何例子進一步證明禪宗這些親歷學習是建構在觀察學習的基礎上提倡?不難。假如我們把審視禪教學法的焦點放大到整個宋代的禪燈錄和禪語錄,就會發現,所有「拈古頌古」、「禪公案」的形成根本就是一種觀察學習行為的完全展現。禪人留下的片言隻字,成為後世禪僧賴以教化學人的教材,由於禪人的教學機鋒呈現出一定程度的開放態度(即open-ended questioning),其又把前人的學習經驗作為學人學習新經驗、新行為、新方法的聯結,公案因而形成。禪師以此指導學人從公案中悟得重要禪理,並以時節因緣隱喻對功能刺激(functional stimulus)作用的認同,輔以善知識的點撥指導,以助學人產生內在的個體認知,證悟禪理。
雖然Bandura提模仿學習、功能刺激作用等這些理論之原意是對青少年學習認知過程的一種系統性描述,但我們認為,這種劃分完全可以被套用在禪宗的象徵授禪法上來分析。上世紀西方的認知學習理論,呈現出一種較清晰化、系統化的概括和分類,填補了教育歷史中的空白部分。這些概括和分類可應用於對不同人在不同學習層面上進行學習活動時各種形態的解釋,為我們研究禪教學、甚至古代各地教育方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方便。今天,當我們用20世紀的西方理論去觸摸1000年前我國的禪教學世界,就會更加發現,禪的教學世界究竟是如此千姿百態,如此耐人尋味。










-300x16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