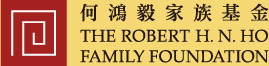口述:法光法師
筆錄:陳芷涵
編按:二零一八年四月,法光法師在香港佛法中心開示,談到年輕時學佛的心路歷程,同時感恩當時曾給法師幫助的張如觀居士。法師從初學佛即信願深廣,並且一直堅持至今,給我們很大鼓勵。法師在文末一再強調張居士的「願力」,一直沒消散,一直推動著他的後代。感謝香港佛法中心授權佛門網轉載。標題為佛門網編輯所加。
今天早上我們特別歡迎從新加坡遠道而來的兩位信徒,張三春和毅宏。剛好他們來到,我想藉此機會,給大家介紹他們的父親,張如觀居士,同時分享我年輕時學佛的一些心路歷程。
他們的父親沒來,因為已經歸西很多年了,但是他的故事很感人。我第一次認識他,是我在去斯里蘭卡之前,在印度那爛陀大學讀書的時候。古那爛陀大學當然已經不存在了,但在其附近有間那爛陀學院。我的梵文最初大部分是在那邊學的。當時他們的父親帶著兒女去朝聖,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就感覺到他非常的真誠。那時我住在一間名為「中華佛寺」的小廟,在那爛陀村的村口;過著很儉樸的生活。那時我已下了決心,要學好梵、巴(利)文,深入經藏,以期日後能作出一些貢獻,令佛法發揚光大。這當中有一些自己難忘的心路歷程。
我年青時非常富於理想,最初感覺到「學問是學佛的障礙」;既然已出家學道,就要放下一切,不應再讀書,鑽研佛學。但後來看到一些刊物、書籍等,介紹一些西方傳教士,特別是幾位天主教的神父:一位是 Louis de La Vallée-Poussin,是比利時人。他的老師是Sylvain Lévi,是法國人;他的學生Étienne Lamotte, 是比利時人 。這幾個人讓我開始了解到,原來他們雖是天主教神父, 終其一生卻致力於佛學研究,而且有輝煌的成就。到今天為止,在全球的佛學界來說,他們還是極有權威,少有佛教學者能超越他們的。
他們身為「異教」的傳教士,卻在佛法中找到意義,在佛學教理、歷史、語言上,幫我們佛子解決了很多難題,作出莫大的貢獻。原來他們都有文學博士、哲學博士、教授等名銜。 他們全部精通佛典語言——像梵文、巴利文、藏文、日文、漢文。後來更加深入漢系的佛典。譬如Poussin, 花了二十年去研究玄奘法師所譯的 《俱舍論》;比對真諦、藏譯等,把它翻成法文。到今天為止,這部翻譯可以說是最有權威性、最好的。要研究毘曇學、俱舍學的學者,這本書是必備的參考,做為依據。除此之外,他還花了十二年去研究玄奘法師糅合眾論師所釋而著的《成唯識論》,並翻譯成法文。此書是中國佛教最寶貴的佛典之一。最初西方學者能接觸到奘譯的《大毘婆沙論》,主要也是他的功勞。從他傳出來的後,西方才知道,原來漢譯的《大毘婆沙論》如此寶貴。他雖然沒有將整部的《大毘婆沙論》翻出來—— 因這部論是很大部的,共有二百卷——但裏面很多重要的部分,他已經都翻譯成法文了;特別是他發表的Documents d’Abhidharma,是 《大毘婆沙論》 的選譯;我看到後非常感動。
Poussin的學生Lamotte,把《攝大乘論》、《解深密經》、《大乘成業論》等幾部重要的聖典,比對漢譯及藏譯,翻譯成法文。從這些翻譯裏所附加的極其大量的註腳中,就可以看出他們佛學知識的淵博。他們的研究涵蓋整個佛教,能引經據典,出處包括巴利文經典、梵文經典、漢文經典、藏文經典。還有從玄奘法師的弟子的註解,譬如普光、窺基等。我不禁萬分慚愧:這些竟然不是我們佛教徒做的,而是外國人又是異教徒對佛學所作的貢獻!非常難得——深深地感動了我。更使我體會到今後我作為佛子的使命:我發願要從新振作起來,為弘揚佛學而認真鑽研佛學。於是思考如何開始。
恨不得一星期之內就成佛!
剛才說過,年輕時的我是很富於理想的。那時真的覺得通通都要放下,不要學習了;恨不得一星期之內就成佛了⋯⋯所以當這樣的情緒到了頂點時,我就決定非出家不可——其他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沒意義了。出家後,我回到了馬來西亞、新加坡。當然我不敢說,那裏當時沒有高僧大德。主要也許是因為當時還年輕,思想不夠成熟,感覺到真正有修行又有佛學修養的導師,很難找到。後來看到美國金山寺出版的《金剛菩提海》,執筆者主要是美國人及一群台灣的佛教徒一起合作寫出來的;內容談到他們如何在金山寺修行。我了解到那些美國人—— 他們這麼有學問,這麼年輕有為,很多出自良好家庭背景,擁有碩士、博士學位——毅然出家,跟隨著宣化上人學佛。導師一句英文都不懂,為了跟他師學習,所以他們要學習中文。他們非常聰敏,學習看中文的經典、學習誦中文的經。看到他們在雜誌中的記載、描述,對導師的讚歎,都可以深深的感受到他們的真誠。所以我就發願一定要到美國去。當然很多人勸我不要去,說「您太天真了,您只是看到外表……」等等;講了很多。我想可能他們與宣化上人的思想有所不同,才不鼓勵我去。但我決心要去,於是就辦了相關的手續,飛往舊金山。
在宣化上人那裏呆了大約八個月,跟他們一起修行。他們日中一食,沒有早餐。每天三點多起床;如果睡過頭了會有人敲門叫您起床。四點上大殿,喝杯水或茶就開始禪坐了,每個小時經行、禪坐、經行……這樣一整個早上,到十點是上供。吃完一天中的一餐,經行唸《大悲咒》108遍後,再繼續禪修,直到下午,各人有各人的工作。我是參加翻譯的。他們美國人很聰明,除了在漢文學習方面有所成就之外,也學習如何修繕寺廟。廟本身是人家不要的倉庫,很便宜的買下,找外面的技術人員來修理、裝修。在這過程中,他們向裝修工人學習,工人走了,他們就可以自己來裝修了。所以他們修行與各方面的學習,都極其真誠精進。當寺廟大門一關上,就變成另一個世界,沒有人外出。
當時我還有點反叛。因為我在圖書館裏所看到的資料,想進一步了解西方傳教士們是如何學習,如何精通這麼多國的語言,又能在佛學上如此出人頭地。我知道柏克萊大學有幾位佛學專家,包括Lancaster和Jaini 教授。最近我在香港大學演講時,提到年輕時曾參學於金山寺,剛好Lancaster 教授就坐在台下;我還開玩笑,說他可以做見證。我年輕時就找過他,跟他談起我重新深入佛學的決心。我當時如此求學心切,金山寺卻又如此嚴格,真逃避不了內心的矛盾。很不容易,才獲准外出到柏克萊大學幾趟。
「學佛而佛學」、「佛學而學佛」,要把兩方面圓融
但回想起來,在金山寺那段苦修的時期,對我來說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也可以說是我人生一個非常寶貴的體驗。在我參與翻譯任務的期間,我有時還有機會在圖書館裏看佛經、佛學論著,以及一些佛教刊物。了解到剛才我提到的那幾位神父,目睹他們在佛學領域裏的偉大成就。所以當時我就把他們當成我學習的典範。我也同時體會到:研究佛學,研究一個宗教的哲理,不一定要像那些「純學者」那樣的只為研究學問而研究;您絕對可以保有原來的宗教情趣。人家異教士都可以,為甚麼佛教出家人就不可以呢?最主是看您內心有沒有真誠與足夠的信願。您的方向決定了,有了定向座標,再多的學問研究,也不會動搖你的學佛心。因你是以「修行」為目的而學問的。從那時候開始,我認識到要「學佛而佛學」、「佛學而學佛」,把兩方面圓融起來。
後來因為當年年輕,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及理想,所以覺得那邊的方式未必適合我。但到今天為止,還是心存感恩及讚歎他們,儘管我們想法有點不同。我感覺第一、好像釋迦牟尼佛的修行不是極端「苦行」;第二、我既已想好好鑽研佛學了,而在那裏看來沒機會,所以我就想離開那地方。宣化上人對我很慈愛。他說:「整個僧團裡只有您一位中國人,希望您能留下來。」後來我還是離開了到洛杉磯的另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共有三個單位。一個是「國際佛教禪修中心」(International Buddhist Meditation Centre),另有一所「東方學院」(College of Oriental Studies),後來改稱為「東方大學」(University of Oriental Studies),現在又改成「佛法大學」(Buddha Dharma University)我在那裏學習過。我住在另一單位「越南寺」。在那裏,我與越南的佛教徒有很好的緣份;他們很照顧、愛戴、支持我。當年,年輕、富於理想的我,是如何知道他們的呢?我是在金山寺的圖書館看到他們的消息的,並了解到「越南寺」的方丈釋天恩法師曾留學日本,並拿到佛學博士學位。
天恩法師和諧可親,非常慈悲。我不認識他們,也沒人介紹。當時身邊只剩下美金兩、三百塊。而我就這麼樣去了,膽子真大。
「東方學院」有位頗有名氣的學者,叫Leo M. Pruden。我聽過他的兩門課;「印度佛教史」和 「俱舍論」;也從他學到了不少西方的治學方法論。當時他已開始將Poussin的法譯《俱舍論》譯為英文;邊譯邊講。由於我一直都關注著印順導師的著作,深受啟發;有時聽Pruden教授講課,覺得有點不太順耳,就引用導師所說,與他爭論。想起來實在應該慚愧。
我到了「越南寺」,跟天恩法師頂禮後,就率直地自我介紹並把我的心願告訴了他。他很慈悲。但美國人是很務實的;入境隨俗,所以他也很務實。他說:「我們可以給您掛單,但是我們沒有房間。」他自己的徒弟每個都要繳租金;但我繳不起錢。我說:我可以睡在佛殿的地毯上。他說可以;但冬天到來後怎麼辦?我說,到時才算吧!就這樣開始。
在天恩法師的領導下,那些越南的信徒既虔誠,又有悲心。他們看到我這樣,一些越南難民們常買東西給我——我要看甚麼書、字典,他們就想辦法去找;也常煮點麵、飯,給我吃。還有「彌陀寺」是整個學院的一部分,他們也煮東西給我吃,還供養我。否則我無法生存。我沒外出,所以也沒花甚麼錢。那時真的非常富有理想,很有勇氣。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得到的熏習是非常寶貴的。今天我感到很慚愧;因我相對上很懈怠。那時候真的甚麼都不想,只想成佛;真的要好好學習,深入佛法,希望有日能像那些天主教神父那樣「深入經藏」。
後來天恩法師也很看重我。他們週日就像我們現在這樣,有念誦、開示。他都會讓我用英語講幾句話。由於他們的德行與慈悲,大概覺得這個年輕有為的法師,頗有學問、很真誠,所以很看重我。
洛杉磯有一間中國人的佛寺,好像叫做「圓覺寺」,是一位香港的比丘尼文珠法師主持的——很多年後,我在志蓮淨苑再見到她。天恩法師每週都會到那邊去開示。但他不懂得中文,需依賴一位居士來翻譯。後來天恩法師知道我是華人,懂得中文,就帶著我去幫他翻譯。當時我的腦筋比較好,很靈活;天恩法師講的,我無須記錄就可以直接翻出。大家都表示很滿意。天恩法師很高興我住在「越南寺」。他跟我說:「您不要離開這裏。如果您想讀博士,繼續深造的話,可以在這裏讀。」 文珠法師也同樣很鼓勵我,表示樂意支持我深造。
下決心要到佛陀走過的地方
但當時我已下了很大的決心,要到印度去。天恩法師跟我說:「您不要走,我跟您辦綠卡。」我說:「不要,我一定要到佛陀住過的地方,佛陀腳走過的地方,也就是印度。」因為我知道印度有個「那爛陀學院」,在那邊可以學習梵文、巴利文及佛學。最後他們也成就了我。文珠法師給了我大約三千美金;越南的信徒們幫我買機票, 還有我的行李箱等等。我就這樣到印度求學去了。這是我年輕的時候,生命中很快樂、很有意義的旅程。今天這些歷程對我的生命來說是很珍貴的體驗。現在很慚愧,不能像當年那樣精進。當年的信願是很深、很廣的。
在印度那爛陀學院讀書時的生活,可以說是非常困苦。「中華佛寺」很窮。當時中國籍的老法師已經不在了。寺裏只有一位老撾籍的法師,很老實、真誠,在學院念博士。我跟他一起住,生活非常簡樸、清苦。他們在寺院裏種點菜;木瓜也用來做菜。因為住在中國寺,他也一起吃素。
這所現代的那爛陀學院,最初十多年,程度非常高,因此馳名國際。很可惜我去的時候, 種種原因下,它的水準已經一落千丈。之前如創校的J Kashyap長老/教授、S Mookerjee教授、N Tatia教授、U Dhammaratana長老/教授等,都已退休了。剩餘下來的,除了以兩位(如Vyas,梵文教授)外,其他的老師,都很令人失望。我當時的求知欲非常的強,很想學,卻在課堂上學不到東西。怎麼辦?我知道在村裏有位叫做Brahmānanda的婆羅門教士,梵文非常好。他沒有家庭;我就請他每天晚上來我們的寺廟;我跟他苦學,給他泡茶、泡咖啡及一點錢。那時候在迦爾格達的一些華裔信徒,有時候來那爛陀朝聖,知道有位法師是華裔,生活清苦,都會拿點供養給我,例如食物、果儀。我是這樣生活過來的。文珠法師說過:「有甚麼問題,隨時寫信給我。」但那時嚴持原則,從來沒求過別人;只要不會餓死就好了。很感恩這位婆羅門老師,讓我學到許多梵文。其實當時自己覺得還不能受用他的學問;因為我問他一個問題,他就可以將整套Pāṇini文法規則,連同註解,全背出來給我聽。我問他一個字的根,他就講解一大堆。我有時真的吸收不了,但學到了很多東西。我的另一位梵文老師,是那爛陀學院的Vyas教授。他現在還健在。我到他的宿舍跟他讀梵本《俱舍論》界品,也學到不少東西。他沒收我錢。
就這樣,我雖在那爛陀學院上課;實際上,梵文主要還是私下跟那兩位老師學的。一年多後,基於種種原因,決定離開那爛陀。但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那爛陀學院的水平,已經一落千丈。大部分的老師又很懶散,令我失望。第二、婆羅門教徒的「階級制度」。儘管我不是他們的一份子,但也看不慣他們那種對所謂的賤民(Untouchable)的輕視與欺凌。所以就決心嘗試前往斯里蘭卡這個佛國。剛好也有過一些善緣,認識那邊的一位法師。於是開始跟他聯繫商討。
就在此時,張如觀夫婦帶著他們兒女到那爛陀朝聖。我馬上就直覺到這位古稀老人的極度虔誠,深受感動。他在印度朝聖那段日子,也過得很清苦。當兒女們覺得那邊的食物無法下嚥時,他總是說:「我覺得很好啊!」除了去拜佛,哪裏都不去。他跟我談了很多關於學佛、修行的問題。後來我到斯里蘭卡就學,每年他都會去看我來兩、三次。有時跟夫人一起去,有時跟兒女去。他不是去玩;都是去朝聖,去拜佛。住在我掛單的寺廟裏;我們就陪著他到聖地去朝聖。
我記得陪他爬「聖山」Sri Pada。那山相當高。他一邊念佛一邊爬;爬到山頂,爬到天亮。當時他的年紀已不小。我們途中都需休息;我們勸他休息,他都堅持不要,使我又一次親身體驗到他的虔誠與偉大。我想生命中看到最真誠的佛教徒就是他了。從他身上——他的身教——學到很多佛法。他在我面前懺悔過幾次;跟我說他年輕時出過家,當時卻了解不到佛法的偉大,有機會學佛卻沒學好,有機會修行卻不懂得精進。後來還俗成家了,兒女一大群。到了晚年,他突然間起了很真誠的懺悔心,很想再出家,環境已經不允許了。他一直很激動,多次在佛前和我面前誠心懺悔。我在他的身上真的學到甚麼是「慚愧」。
意志堅強,不願攀緣任何人
我在斯里蘭卡讀書也沒人支持。但意志很堅強,不願攀緣任何人。張居士了解我後,就一直支持我。我要看中文的佛書,他馬上就從星洲寄過來,也常寄點錢給我;包括我後來成為講師後,住在一個破廟, 要修理,他都盡力支持我。那時他年紀也大了,在新加坡過年過節,兒女們給他的紅包、禮物、好吃的東西,他都存起來。等我到星洲弘法時,全部供養我。皈依了我,跟我學打坐。他開始認真地閱讀經典;看不懂的,就寫信問我。
後來他不幸中風。他對我信心極堅強,又多給了我一個因緣,從他具體的例子親身體驗到經中所說「信」的力量。加上他的真誠、懺悔心,我真的能親證到信力的不可思議!他中風時要家人立刻打電話找我。可惜當時因通訊不好,電話也很難打通,不像現在有電郵、微信之類的方便。我無法馬上到,就跟他念經、真誠為他求三寶加被。然後買到機票,到了新加坡,又再為他誦經、祝福、開示。
他說他有個心願:儘管身不能出家,還是心想出家。他想要受「八關齋戒」。雖然依照傳統,「八關齋戒」 一般是在寺中一日一夜授的。但我決定成全他,帶他到新加坡斯里蘭卡佛寺(Srilanka Āramaya)的菩提樹下,跟他授了八戒,並與他一起坐禪。據說,當時醫生已建議他交代好後事,準備遺書之類的。他自己聽醫生這麼說,也很認真。但是,就因為他的真誠、信心、懺悔心,所以他渡過了那一關!
我回到斯里蘭卡不久,聽說他慢慢好起來——是個奇蹟——也多活了很多年。之後,還依樣每年最少到斯里蘭卡朝聖一次。如此真誠,如此有慚愧心;當時也感動了他的兒女們。但當時他們還年輕,不懂得佛法的寶貴,不懂得甚麼是修行。幾十年以後,因緣成熟了,他們也感受到父親的感召,開始真誠的學佛,到斯里蘭卡拜佛,也去了好多次。他們還學父親那樣來護持我,了解我如何弘法,非常難得。所以他們今天特別來看我,我就想與您們分享這個故事。這就是佛法,真正的佛法。我是真正的體驗到:甚麼是「真誠」, 甚麼是「慚愧心」 甚麼是「信心」。張如觀居士的德行與無比的、廣大的信心,讓他能渡過了難關。而他的感召力量,他的「願力」,一直沒消散,一直推動著他的後代。今天,他的兒女們都承續了父親的「信願」。